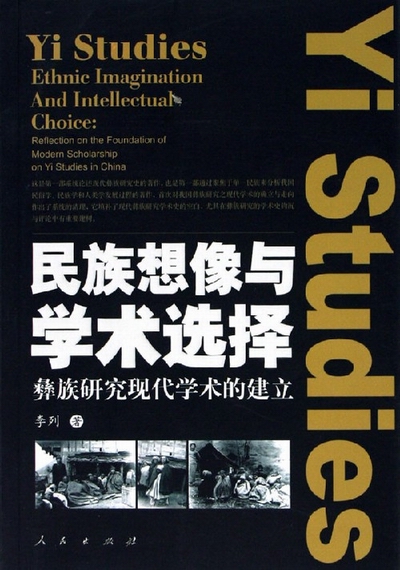
国际彝学已走过了百年历程,并且成为一门跨学科的国际性“显学”,但至今没有一部全面清理其学术发展轨迹的学术史。李列博士的这部新著,以“问题与个案”为论纲,以“学术转型”为关节点,以梳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研究过程”为主线,站在社会─历史─文化的多重维度上,以“他观”与“自观”为研究主体在学术视野和叙事话语上的双向统合,从“印象之学”到“事实之学”,从现代民族主义背景的宏通观照到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有效地将发轫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彝族研究及其间纷纭复杂的历史变革与社会思潮、人物和事件、著述和观点汇聚为一个步步深进的学术阐释空间,其中既有“史”的透视,又兼有“论”的引申,首次对我国彝族研究之现代学术的确立与走向作出了系统的清理,在本土彝族研究的学术史钩沉与论评中总述创获,彰明源流,形成了如下多方面的突破:
一、在资料学的发掘上:该著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中的重要期刊和相关文献进行了深细的发掘和爬梳,广泛搜求了大量堙没在历史风尘中的文本和成果,首次重点考证了彝族研究学术史这一特定领域在特定时期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全面梳理了代表性学者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彝族研究作为(汉语)学术资源的特殊优势与发展空间,以探寻丰富和发展这一学术传统的创新途径。应当说,彝族研究可称之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数民族研究从初创到发展的一个缩影。该著从资料学这一基础性环节上,为族别研究的学术史写作,提供了深掘学术资源的一个范例。
二、在方法论的架构上:该著作为一种“史”的叙事性阐释,作者首先以学术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框定自己的“工作方法”,即如作者在博士论文答辩时所概括的“研究几位学者”、“突出一个‘团体’”、“分析一个时段”、“选择两个视角”,以实现全书的工作目标。作者以“问题与个案”为论纲,举凡民族与国家,西学与国学,边疆与边政,国难与学术,官员与学者、师承与治学、他观与自观等,都是关系到现代学术之建立及其走向的关键问题,贯穿着作者对这段时期学术深进的历史思考,如“四川省政府施教团”的考察,体现了敏锐的学术眼光和事件阐释的理论力度,并藉此勾勒出二十世纪中国彝族研究作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学术在其发轫和开创阶段的学术史之全景,也为引领、补阙和完善我国彝学学术史构建了一种可资参照的工作框架。
三、在研究主体的观照上:该著首先聚焦于杨成志、林耀华、马学良等近二十位彝族问题研究的大家,其中既有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又有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通过对这些有着不同学术背景、不同经历的学者及其治学道路的叙述和分析,探讨他们在借鉴西方学术理论与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治学方法两方面的经验和局限,从而勾勒出现代学术史某些复杂的社会情境、个性化的学术实践,以及群体性的研究布局。进而作者转向本民族的知识精英与社会中坚,以岭光电和曲木藏尧为案例,从比较的角度,直面有着不同学术视野、不同文化身份和不同学术诉求的研究主体与学术行为,在“他观”与“自观”的双向互动中,结合学术访谈讨论了主客位研究的知识谱型与实践策略,即使是对“局内人”的考察也贯穿着不同社会角色与不同个性化实践的成因分析,从中究问学术发展过程中的知识图式和研究视野的多重变化。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作者所选对象,基本覆盖了中国彝学研究乃至现代学术研究中无法绕开却又因种种原因被“遗忘”或“淡忘”了的重要学者,并提供了大量翔实而生动的实证资料,这便更为全面而系统地从研究主体这一知识生产的重要环节突显出中国现代彝学研究及其学术格局。因此,就“现代学术的建立”而言,作者聚焦于“彝族研究”,实际上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了彝学研究在中国本土化的史路历程。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李列系云南个旧彝族,过去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小说研究,2001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刘铁粱教授指导下攻读民俗学博士学位,其间个人的学术道路也随着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增强而发生了重要的转向,这部著作虽然是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但就其选题、论域和研究方法而言,也得益于他前期关注现代学术史的知识积累和治学经验。就我个人所知,从问题意识的确立到论文写作的推进,其间历时近四个年头,作者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心血,其工作态度和求证精神是难能可贵的。针对现代中国彝学研究中的关键性缺环,他力图广泛搜求和系统梳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各种学术信息,在北京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等资料重地潜心阅读,仔细搜罗,占有了大量的现代学术资源,为其论述构成了坚实的资料学基础;同时还对相关的彝学研究者进行了认真深细的专题访谈,其间得到了岭光电先生和曲木藏尧先生的家人和亲友的鼎力支持。这种方法论上的文献研究与口述史的并重,将文本阐释和学者个案法统合为互动性的研究策略,使他在“现代彝学”的学术史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方向,先后发表了《现代彝学的建立与学术转型》、《彝族指路经的文化学阐释》、《现代学术视野下的彝族研究》、《现代学术史上的彝族主位研究:以岭光电和曲木藏尧为例》、《学术中国化思潮与现代彝族研究》、《“施教”与“治夷”:凉山彝族调查报告研究》、《现代期刊与现代彝族研究》等论文。通过以上的学术实践和博士学位论文的完成,对相关的前人论述进行细致分析,对每一发展阶段的彝族研究特点和规律进行综合论述,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彝族研究史的细部面貌和整体概况呈现到了我们的面前,弥补了国际彝学研究中的这一学术缺憾。
作为首部在彝族研究这一跨学科领域中的治史之作,其学术难度和挑战性是不言而喻的。在我的知识范围内,觉得彝文文献、汉文史料乃至外文文献方面之遗珠、相关学者的师承关系、治学道路及其评价定位、学术史的反思与学术精神的重构等方面也还存在有待商榷、充实或完善的地方。从全书来看,或许是过于注重“时间”与学术史之间对应关系,作者在材料的取舍和详略方面也不无值得推敲之处,例如,马学良先生的《历史的足音》与《彝族经籍文化辞典》都是其晚期完成的重要成果,但与其“新学术之路”和前期研究不可或分,在“学术史”里也应该得到相应的反映;再者,对于“中央研究院”在我国现代学术体制的建构中的作用及其在边疆民族研究中的“国家行为”与学术群体之形成的相关讨论尚嫌薄弱。但是,毕竟瑕不掩瑜。该著不仅第一次为我们系统描绘了中国现代彝学从发端到发展的全景,更为我们提供了学术史反思的系统参照和评价体系,从而为国际化学术格局中的中国彝学研究及其研究范式的转换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可谓 “功莫大焉”。
总之,这一系统性、阶段性的族别研究学术史,既是有贡献的劳作,也是有价值的成果;既有交叉性、综合性的跨学科性质,也有学科发展的基础性和前沿性意义。作为同道,这里我要感谢作者的努力和辛劳,让我们得以系统领略中国现代彝学研究的学术成果、学人行迹和发展格局。倘若我们不能对这一时期的中国本土彝族研究有深入的理解,我们的中国彝学及其学科建设就会缺乏根基。相信随着该著的出版,其重要的理论视界和实践方法对推进中国彝学、国际彝学乃至中国少数民族的族别研究史都会提供有益借鉴。作为同道,我也希望李列将以此书的面世作为自己治学道路上的一个新起点,在彝学研究的学术史方向上再接再厉,不断深拓。我们这一代学人,只有以更高远的学术理想、更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更扎实的学术实践来承续和发展彝学研究前辈们的未竟事业,才能在彝学研究的国际化学术对话中找到中国本土学术传统的意义世界。谨此兼与作者同勉。
2006年5月




